贴子已被锁定
梁佳认定妈妈这辈子除了跟爸爸结婚,就再也没有跟别的男人恋爱过。可是现在,她知道了,除爸爸之外,在妈妈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个叫吴千岸的男人。他甚至有那么一瞬间竟怀疑自己不是现在的父亲亲生的而可能是吴千岸的孩子……
一
梁佳是在同系的老教师范东坡家里看到那张老照片的。
那张照片用两个镶金的对角固定在黑色的硬纸背景上,约五寸大小,上面有十来个人,照片顶端印着一行横写的白色手体字“某某省某某县红崖乡四清工作组干部留影,1965年12月”。照片好像是在一个类似于庙的那么一个建筑物前面照的,屋顶上是光秃的枝杈,人人都穿着棉袄棉裤,脸上带着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有的单纯和真诚。年轻时代的范东坡在照片的左上角,脸上带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微笑。
梁佳之所以在那张照片前停下来,是因为她发现右上角那个年轻的女子很像自己的妈妈。那女子穿着棉袄,外面大约是罩了一件方格子图案的罩衫,在照片上显得黑白分明,她扎着两条麻花辫子,显得比照片上另外一个短发女子更有灵气一些。
梁佳越看右上角那个年轻女子越觉得她像自己的妈妈,那月牙形的眼睛,那小圆脸,还有稍稍自来鬈的头发,一个人身上的某些特征从生下来到老去都是不会变的。
范老师,这个右上角的女的是谁?梁佳把影集搬过去,有些激动地问范东坡。
范东坡先找到老花镜来戴上,瞅了一下照片说,哦,这是我刚刚大学毕业那年照的,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都34年了,这个右上角女的,怎么了,难道你认识?我记得她姓顾,叫顾小白。
她是我妈妈!果然是我妈妈!梁佳几乎是喊了出来。
范东坡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把梁佳打量了一遍说,你竟然是顾小白的女儿?你跟我同事几年了,到今天才知道你竟是我的老同事顾小白的女儿,嗯,眼睛蛮像的。
范东坡感慨万千地看着照片,上面一共有十二个人,十男两女。范东坡指着一个说一个,这个女的叫汪云清,家里说是什么资本家,文革没少挨斗。这个是老孙,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现在省科学院,前两天我还见过他。这个是老骆,是跟我一起从师大毕业的,现在去美国了。这个嘛老苏,老苏在哪里,我还不清楚,多年没有联系了,爱吹牛。这个叫什么来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名字了。还有这个,是从林学院毕业的老满,四清工作完了以后就没有联系过,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原先是分到园林局的,他年纪比我们都大些。那时候属调干生,肯定早就退下来了。这个,这个嘛,姓吴,叫吴千岸,是从哈工大毕业的,浙江人,最初是分在了省机械研究所工作,文革时出了事,现在不知在哪里,哦,对了,据说他跟你妈妈很好。当说到吴千岸跟梁佳的妈妈很好的时候,梁佳注意到范东坡嘴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意。
二
梁佳仔细看了看那个叫吴千岸的男人,他站在梁佳妈妈前面一排的中间位置,那时的照相技术不怎么好,他的脸上有些跑光,比起其他的人来,他的脸明显不够清楚,即使是这样,还是能看出他是一个中等个子、清瘦文弱的男人,戴着一副白边眼镜,他笑得很灿烂,他的嘴巴张得很大,看来他本来就长了一个大嘴,那嘴大得实在有些夸张了,使梁佳觉得如果不是有两边的耳朵挡着,那嘴巴大笑起来,简直能咧到后脑勺去,能绕脑袋一圈。梁佳一直认为大嘴的男人性感,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没有这个词语的,即使有,也不会是褒义词。
梁佳觉得从范东坡的表情来看,他说的这个男人跟妈妈很好,一定该是那种男女关系的好了,那从时间上来看,一定是在妈妈认识爸爸好几年之前的恋人了,可是从小到大从没有听妈妈讲起过她的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个男人。
梁佳再看照片上的妈妈,同时在心里计算了一下,那时妈妈应该是刚刚满20岁,脸庞那么滋润饱满,像一朵大百合花,照相的那天看来有风,吹得她额前的头发稍稍有点凌乱地朝一个方向飘着,看上去倒显得更加妩媚了。一定是前排中间那个叫吴千岸的男人使她脸上洋溢着这样动人的表情吧?那是1965年冬天的风,它在那张照片上,它在妈妈年轻的脸上,吹拂了整整34年了。
自梁佳有记忆以来,妈妈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中年妇女形象了。梁佳记得在她小时候就常听到妈妈说类似的话“这种衣服我这个年纪怎么穿得上身,颜色过于鲜亮了。”是的,自从梁佳记事以来,妈妈就逛中老年服装店了。
所以梁佳认定妈妈这辈子除了跟爸爸结婚,就再也没有跟别的男人恋爱过。可是现在,她知道了,除爸爸之外,在妈妈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个叫吴千岸的男人。
范东坡听说梁佳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就说,这张照片当时每人发了一张呀,你妈妈也有一张的。不过范东坡答应说,他会想方设法找照相馆翻拍一张送给梁佳的。
梁佳想,妈妈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会喜出望外的。
大约一周以后,范东坡果然把照片翻拍了一张,给梁佳送了来,梁佳觉得翻拍的效果还不错,跟原版相比,不差上下,当然吴千岸的脸上还是像原版一样是有些走光的。
三
梁佳放暑假回到位于千里之外海边的父母家的时候,把照片带了回去,给妈妈看。妈妈见了照片很高兴,拿在手里仔细瞧了好半天,说自己以前也有这张照片,后来弄没了。当梁佳把吴千岸指给她看的时候,妈妈竟然像小姑娘一样脸红了,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埋怨女儿多事,翻拍这老古董做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
在梁佳的百般纠缠下,妈妈才讲了她和吴千岸的一点故事给她听。令梁佳感到惊讶的是,她小时候还见过这个哈工大或者说吴千岸———
1977年初夏的省城南郊,空气里到处飘荡着麦香,那是一种值得信赖让人心神安宁的气息。一个叫吴千岸的男人从这个省城的火车站出站口出来,看着这座自己离开了十年已经变陌生了的城市,并没有急于回不远处自己的原单位,而是进了郊区客车联运站,买了一张车票,出发到南郊去。他要去那里寻找自己的恋人。她叫顾小白,他们是在四清工作组里相识相爱的,相爱两年后,他们本来都准备结婚了,可是他突然被捕入狱,入狱的原因是他在下工厂辅导工人文化课的课堂上犯了特大政治错误。那时候文革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们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革命口号。当时吴千岸下去教课的那个工厂别出心裁地规定,上课迟到了,学员站在门口不喊“报告”,而是要喊一声“毛主席万岁”,讲台上的老师也不说“进来”,而要说一声“万万岁”,就等于允许学生进来了。结果有一个年轻调皮的工人老是上课来晚了,吴千岸的思路老是被他打断,所以吴千岸很不高兴,当那个工人又一次迟到了,站在教室门口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吴千岸不想让他进来,就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不万万岁”,结果全体学员哗然,吴千岸就被当作反革命揪了出来,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在监狱里他曾经三次试图自杀未遂,还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当然他还是活下来了,活到了现在,可是他不知道生活还属不属于他。
客车渐渐驶出了城外,视野里出现了正在收割的麦田,这个男人心里非常忐忑,他不知道他的恋人是不是还在等着他。他的心里一会儿兴奋一会沮丧,让一个女人等自己十年,是不是太艰苦卓绝了?车子就在他的悲喜交加中翻过几道山梁,最后驶进了南郊汽车站。
他下车后凭记忆找到了恋人工作单位的宿舍,看到了那些红顶的旧房子,十年前他来过这里,可是十年过去了,他不知道她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在大门口,他想还是找个人问一下比较妥当。他看到了一个拿着一束蟋蟀草在编织什么的小姑娘,七八岁的模样,就问,小朋友,我向你打听一个人好么,你知道一个叫顾小白的阿姨是不是住在这院子里?小姑娘抬起头来,她长着一双月牙般弯弯的眼睛,她说:顾小白不是阿姨,顾小白是我妈妈,她现在就在家里,我领你去吧,叔叔。当时那个男人呆住了,但仿佛又在预料之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不知道是该离去还是跟着小姑娘往前走,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该出狱,他甚至想重新回到监狱里去,把牢底坐穿。
小姑娘对他很热情,拉起他的手就往院子里走,这是他的恋人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她管自己叫叔叔,是的,不叫叔叔又叫什么呢,他也就只是个叔叔吧。小姑娘嫌他走得慢,说叔叔你快些走快些走,而这个男人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地拖着。后来总算挪到了一个房子前面,门口有一棵大泡桐正在开花,那种香甜沁人心脾,可是在那男人闻起来却是伤心的气味。他觉得这气味一下子钻进了他身体的最深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气味了。
到了家门口,小姑娘松开这个男人的手,一边喊一边朝屋门口跑去:妈妈,来客人了,来了一个叔叔。一会儿麦秸编的门帘掀开来了,一个抱着一周岁多的孩子的妇女走了出来,她的后面还怯生生地跟着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这三个孩子全都长着月牙形的眼睛。那天梁佳的爸爸不在家,出去了或者上班了,妈妈嘱咐了梁佳几句,让她好好和大妹妹玩,就抱着小妹妹,跟着那个男人出了宿舍大院。
四
爸爸回到家的时候,妈妈还没有回来。妈妈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爸爸问去了哪里,妈妈就直说:去了南河滩。南河滩是南郊一条水量很大的河,是由山间泉水汇聚而成。两岸碧草青青花盛开,是个很好的去处。梁佳小时候想当然地以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唱的就是她家门口这条河。
那天晚上家里的空气很沉重,三个孩子早早睡下了,梁佳装睡,她有时半眯着眼偷看一下大人,爸爸使劲抽闷烟,妈妈小声地哭。梁佳猜测这肯定跟今天来的那个叔叔有关,那个叔叔没有走,听说住在了家附近的红旗招待所。
第二天,那个叔叔趁爸爸不在家时又来了,她和妈妈又去了南河滩。第三天,那个叔叔是趁着爸爸在家的时候来的,然后爸爸和他两个人出去了,说是去工农兵饭店吃饭。妈妈没有去。最后的结果是,爸爸回来了,对妈妈说,我们以后好好过,把三个孩子都带大。然后妈妈又哭了。原来是爸爸给那个叔叔在工农兵饭店摆了鸿门宴,那个叔叔答应从今往后再也不来找妈妈了,答应终生不见面。妈妈在这之后还收到过这个叔叔写来的一封又一封信,妈妈都像向组织汇报一样地给爸爸看了,妈妈一封也没有回,最后信就不再寄来了。那个男人的单人照,还有他与妈妈两个人的合影,在当年妈妈决定与爸爸结婚时,就都统统毁掉了,她只保留了一张四清工作队在红崖乡的合影,那上面有那个人,她可以偶尔正大光明地拿出来看看他,而现在她痛下决心决定毁掉那张合影了。她是当着爸爸的面撕掉那张有吴千岸的合影的。撕的时候,她面容平静,横着撕竖着撕,撕得很碎很碎的,撒了一地,然后她冲着梁佳喊,佳佳,去锅里拾馒头来,吃饭了!两年以后,梁佳全家就搬走了,去了千里以外的一个海滨小城。
梁佳听完故事,对妈妈说,我一定找到吴千岸,还要安排你们再见上一面。
妈妈指着梁佳的鼻子说,你个死妮子,神经有毛病!
梁佳一心想知道吴千岸的下落,就婉转地托范东坡帮忙打听一下。
五
梁佳在寻访当年吴千岸和妈妈的莫须有的踪迹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竟怀疑自己不是现在的父亲亲生的而可能是吴千岸的孩子,父母是相识一个月后闪电结婚的,自己生在他们婚后的第九个月,这也未免太快了些。梁佳还想到,父母和两个妹妹全都长得个头很高,身架也大,是典型的北方人的模样,惟独自己长得过于小巧了,所以难保没有南方血统。不过瞎想到这里,她自己也笑了起来,觉得自己未免也太爱编故事了。
范东坡有一天在教学楼楼梯上遇到了梁佳,对她说,我打听到吴千岸的消息了。
梁佳说,怎么样,他在哪里?
范东坡说,吴千岸出狱后很快就调回了浙江老家,在杭州的一个科研所工作,可是他八年前就去世了,享年48岁,到死也没有结婚。
梁佳愣在那里。
梁佳把吴千岸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在那头没说什么,只说,孩子,把电话扣了吧,我累了,想歇会儿。
后来梁佳每次回家都想再找出那张老照片合影来看看,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影集里没有,妈妈放针头线脑的月饼盒子里也没有,她甚至连床洞子里都找了,连钟表后头都找了,但是都没有找到。她试图问妈妈那张翻拍的合影到底到哪里去了,但又觉得问了也是徒劳,她既然存心要藏起来,那问她也是白问。
后来梁佳就渐渐把那照片给忘了。
又过了一些年,爸爸妈妈都跟随着二妹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梁佳在变卖处理父母在国内的房产时,想把一些没价值的旧书旧杂志卖掉。忽然在一本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物般的旧书里,飘落出来一张黑白照片,天哪,正是那张四清工作组在红崖村的合影。梁佳很高兴又找到了它,原来妈妈把它藏到了这里。
可是当梁佳仔细去看那张照片的时候,却不禁大惊失色,前排中间的吴千岸和后排右上角的妈妈都不见了,他们原来的位置空了出来。照片上并没有任何涂抹和刀刮的痕迹,吴千岸空出来的位置的背面是站立在他后面的女孩汪云清棉袄的前襟,妈妈空出来的那个位置的背面露出来的是那座庙的一扇小窗户。梁佳坐在地上,惊得久久不能起来。(羊城晚报2006-0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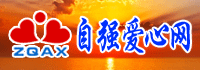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小飞侠
帖子:1750
精华:30
积分:16454
金钱:27454
金币:0
魅力:9296
威望:0
登陆:335
注册:2007/4/5 13:51:22
近访:2010/8/25 14:55:41
在线:
等级:小飞侠
帖子:1750
精华:30
积分:16454
金钱:27454
金币:0
魅力:9296
威望:0
登陆:335
注册:2007/4/5 13:51:22
近访:2010/8/25 14:55:41
在线:
 Post By:2007/8/12 7:40:5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8/12 7:40:5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