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子已被锁定
对于密西西比州的布兰登来说,五月份就热成这样是不正常的。星期天上午,妻子帕特和我坐在我们平屋顶上喝咖啡,慢啜细品。南边地平线上,雷雨云很快聚成崇山峻岭似的云团。空中一丝风儿也没有,潮气很浓,手掌心都可搓出水来。
喝完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闪电狂舞着划过地平线,雷声隆隆,遥远而低沉。不久,第一阵大雨扑来,把我们赶回屋里,恰逢电话响了。帕特拿起话筒,在这阴郁的天气里,她的脸上露出了绝无仅有的欣喜。
打来电话的是我们的儿子戴维,军用直升飞机飞行员。三个月前他自立谋生了,被派往南朝鲜,执行任务一年,驻扎在非军事区附近。
戴维故意说得很高兴,反而使我们更清楚地感觉到了他的真实心境。二次大战期间,我作为一名士兵,把漫长的时间打发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孤岛上,实在知道严重的思乡病有什么样的症状。
渐渐,交谈像良药一样提高了我们的情绪,接着,电话机旁的窗外响起了一声霹雳。
“什么声音?”戴维问。“炸弹吗?”
“没什么,打雷。”帕特说,“这里下雨都一个星期了。”
沉默。
“戴维,”我问,“你走了吗?”
“我在想妈妈说的话——‘没什么,打雷’,可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最想念的什么,许多的士兵说他们所失去的是什么?是故乡的雷声。我们这里下雨下雪刮风,可从来不打雷。”
“爸,记得我小时候吗?”他接着说,“我们俩是怎样躺在地板上聆听雷鸣的?为了我不害怕,你是怎样谈笑风生的?”
“记得。”我说,努力克制自己,不让喉咙发哽。
“现在能和你一起听一听雷声就好了。”他轻轻地说。
刚刚打完电话,我就拿上我的磁带录音机,高尔夫大伞和一把木椅。“我出去给儿子录下一些雷声。”我对帕特说。
“鲍勃,邻居们会说你疯了。”
“戴维不会。”我说,走了出去。
电光闪闪划过天空,如同焰火大表演,我坐在暴雨中的大伞下,录下了半小时密西西比最好的雷声,孤独的士兵永远也听不厌。第二天,我把磁带邮寄给戴维,简书:“特别礼物”。
三星期后戴维又打来电话。这一次他已经心平气和。“爸,”他说,“你肯定想象不到我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我邀请朋友们到我房里举行了一次雷声晚会。听录音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都一样。开始是寂静,随后是一声悲哀叹息,以为是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声。可当大家知道这是故乡的声音时,心情立即好转,我们如释重荷,晚会变得非常愉快,真不知该怎么说,这磁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说,“现在我安心了。谢谢你,爸!这礼物真的不落俗套。乡音解乡愁呵。”
帕特和我也获得一种特别的回报。戴维在朝鲜余下来的八个月里,我们发现自己竟在渴望着雷暴雨。再也不把它们当作倒霉的天气而感到压抑愁闷了,我们开始对暴风雨另眼相待。每一阵隆隆的雷声,都缩短了我们与距离家门的儿子之间的距离。
哪怕雷声响在明尼苏达,如今戴维当战斗机教练员的地方,它仍然是天赐神授。雷声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总是心心相连的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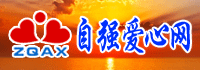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Post By:2007/8/30 21:33:4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8/30 21:33:42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