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子已被锁定
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喝起酒来颇有当年“刘伶喝酒不留零”的气概。隔三岔五,母亲就要去街上装回一桶掺水的散酒。父亲在做农活的间隙,喝酒多于喝水。孩提时代,我就主张父亲戒酒,父亲总说:“闲茶闷酒无聊烟,喝酒因为我闷啊,就这点嗜好,戒了咋成?”事后想想,父亲是“闷”的,他六岁时候正赶上自然灾害严重的1959年。那一年,大别山北麓、淮阳一带,颗粒无收。父亲失去了众多的亲人,偌大的家庭只剩下母子两人相依为命。为了逃荒,父亲跟随祖母一路乞讨从中原辗转到了东北。多年以后,父亲返回到家乡,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困境中重建家园。父亲借了辆平板车跑运输,攒了钱,建了三间土茅寮,又娶了有精神病史的漂亮妻子,养育了四个孩子。父亲一直想办法努力挣钱,在侍弄田地之余,烧过砖窑、磨过豆腐、卖过凉皮。像陀螺一样旋转着的父亲,经常在腰带上系着一个类似林冲枪挑的酒葫芦。父亲说,酒水为他解渴提神壮胆长劲,酒陪着他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日日夜夜。
似乎该我吃的苦都被父亲吃了,我一直幸运又幸福。20岁就大学毕业的我,坐在一家事业单位的办公室里,月薪比父亲稼穑一年的收入还多。似乎该我喝的酒也都被父亲喝光了,我一直对酒精过敏。家里总备有两袋以上的黄山毛峰或太平猴魁,这是爱人从娘家带回的特产。每当有客人到来,我总会自豪地为他们沏上一壶,再鼓吹一番:此茶叶产在皖南山区海拔千米之处,天天浸在云蒸霞蔚之中,故茶芽柔嫩叶片肥厚,汤水清中带黄,闻之香馥若兰沁人心脾,喝之齿间流芳回味无穷,乃茶中极品也。在我的感召下,许多朋友都把茶当成饮品的第一选择了。久而久之,我成了饕餮香茗之徒,一日不饮就感觉食之无味寝之不安。这倒也让我理解了父亲与酒的不解情结。
我以为父亲今生离不开酒了,没想到在弟媳妇进门并生了个大胖小子后,父亲竟戒了酒。父亲解释说:“孩子大了我不累了,孙儿绕膝我不闷了。”父亲的胃病加重了,儿子、女儿、媳妇们为他买蜂蜜洋参了。但父亲似乎不买儿女们的账,洋参留给了母亲,蜂蜜分给了孩子。自从侄子读铚城幼儿园后,父亲便常去街上茶馆歇脚。不久,父亲就沉湎其中乐不思蜀了。铚城茶馆历经六百余年沧桑,如今演变成了游艺场所。拉弦、说书、下棋、打扑克、讲故事、说笑话的乡民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品着香茗谈笑风生。父亲不善言辞,在茶馆里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和看客。对父亲而言,品着一壶用龙须泉水煮泡的绿茶,听着三教九流用家常俚语编织的生活曲调,不啻是一种享受。
前不久,我携爱人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父亲泡上一壶铁观音,同我把“茶”话桑麻。父亲痛说的不是芝麻绿豆,而是革命家史――年轻时,为了能够“食果腹衣蔽体”,为了日子不比邻居差,父亲几乎没有睡过天明觉,总是五更就起床做工了;中年时,父亲渴望把每个子女都培养成大学生,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明白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读书的料;到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目睹一些朋友归于西天,知晓了所有的追求都是过眼“尘埃”,只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我忽然发现没有上过学的父亲此时正向着佛家清心寡欲随缘随性的境界前进。
夜深了,茶凉了,我往茶壶里加些沸水,茶叶又一次上下沉浮,一缕更醇厚更醉人的茶香袅袅升腾。记得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屡屡失意的年轻人来到普济寺,寻求释圆大师的慰藉。释圆吩咐小和尚分别用温水和沸水沏铁观音茶,结果温水沏过的茶没有香味,而多次注入沸水沏过的茶却清香不绝如缕。释圆大师诱导青年人说:世间芸芸众生就如同沉浮的茶叶,只有那些栉风沐雨的人,在沧桑岁月里几度沉浮,才会有那沁人的清香啊。我眼前的父亲,这个仅有166厘米高的普通男人,这个曾经被我无数次埋怨的父亲,在半个多世纪里,死了父兄,逃到东北,吃过窝头,住过茅庵,建了楼房,育了栋梁……
我终于明白,父亲也是一杯酽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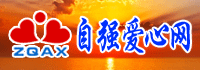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Post By:2007/8/30 21:45:4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8/30 21:45:43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