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隍庙,石华印社坐落其中;不大的工作室,名曰萃砚斋;窗外是秦腔抑扬顿挫的鼓乐声。窗外戏里人生,屋内人生如戏,都是滋味千般。戏音缭绕、书画作陪,空气里飘逸的都是艺术气息。年近九十的篆刻艺术家、齐白石入室弟子骆石华就在这里接受了我的采访。
梅花香自苦寒来
骆老年近九十,从艺六十余年,精通印学、书法、诗文和金石,亦被尊为陇上篆刻巨擘。
同恩师齐白石一样,骆老也出身寒门,少小为生计所忧,饱尝人间甘苦。踏入篆刻的行当,起初不过为糊口之需。地域冷寂,却也艺匠芸芸,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学徒走到今天,绝不是歪打正着。骆老刻印有释:“艺无止境”、“默默耕耘”。
20世纪40年代,他做了三年版刻学徒,二十来岁的青年,天资聪慧也勤于自学,很快显露出艺术天赋,得到了诸多陇上艺术大家的赏识和提携。范振绪、水梓等,都是当时甘肃书画界的泰斗,偏偏对这个小学徒格外垂青。学徒期满,他们资助他挂牌开起了自己的书画印社,从此往来无白丁,他与更多书画名人结交往来,汲取切磋,进步颇大,小有名气。
50年代,他已备受甘肃界内推崇,也是时候走出去汲取更丰富的养料了。在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和老友范振绪的推荐下,他负笈京华,拜入齐白石门下。白石老人当时已90高龄,深居简出。骆石华操一口兰州话,在门人好奇的眼神中呈上介绍信,大约在上午九点,齐白石的大门终于向这个风尘仆仆的西北青年敞开了。
半生坎坷半生笑
还没进入二门,就见白石老人拄着拐杖迎了出来,边走边说“远道而来啊,邓将军的信我看到了……”。骆老讲述的声音悠扬平缓,我低头记录,等待下文,片刻的沉默。突然反应过来这平缓的语调绝非年迈的迟缓,抬头时,骆老正努力控制情绪,眼泪却依旧潸然而下,“我一个穷孩子,童年吃了那么多苦……”。他几次说不下去,停顿、喝水,努力恢复平静。
骆石华搀扶着白石老人进了书房,见面礼是西北特产葡萄干和果脯,白石老人高兴地说:“我前夜梦见有仙客从西方而来,带了仙桃送给我,没想到今天你就来了”。尝了一口果脯后,老人又说,味道和梦里的一样,酸溜溜的。
对骆石华来说,齐白石不仅仅是大师。他是神,是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偶像、楷模,是此生想都不敢想能接近的传奇人物。可大师不仅坐在了眼前,还待他这般谦和宽厚,那西方仙客的梦,据骆老想来,也是白石老人为安抚一个忐忑青年的拘谨而随口说的吧。命运如此大的惊喜和震撼,给骆老留下了一生都抹不掉的记忆。讲起恩师,他数次哽咽。从他克制不住的情绪里,我不仅读出了他对恩师的感念,也找到了他半生坎坷的影子。
像他这个年纪的人,极少有没经历过惊心动魄苦难的,他亦不例外。他能吃苦,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生存所需。然而他只是偶尔提及苦难这个名词,却没有举任何的例证,以至于我的记录里一派天时地利人和的顺畅,仿佛他占尽人间好事。常理、直觉、传闻,还有他眼神里偶尔闪过的幽思却在说,事实并非如此。
少小家贫、七灾八难,甚至九死一生,用他的话说,什么苦没吃过。可他不抱怨不嫉恨,他记得的都是让他感念的事,哪怕隔了五六十年,那些细节都不会有丝毫的褪色。我原本有些惊讶他缘何能有那样清晰的记忆,我也在等待他讲述一些坎坷的经历,好让我的记录与小标题相配。但他把坎坷都淡忘了,他所经历的磨难都刻在他的肌肤里,融化于他的眼神中,它们如影随形构成他生命的沧桑气质,却独独不在他能讲述的细节里。没有人能忘记过去,他也一样,但他不去记。他摇摇头,不提了,把所有的磨难缩减成一个快速闪过的画面,在极短的欲言又止的瞬间挥手抹去。“越不聪明越快活”,更何况他还有他的世界,有他的王国。
就快九十岁了,他依然眼不花、手不抖,书画篆刻一样不落。他的生命给了他足够丰富的底蕴,他的作品亦庄亦谐、风格多样,透着他丰富生命的体验。“半生坎坷半生笑”,那半生的坎坷都藏在半生笑的后面,笑与坎坷对比,才见程度。童心不易得,智慧都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一切“谈何容易”,但“刻石入禅”,自然“一生可口嚼石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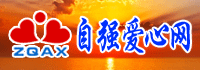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Post By:2008/3/19 9:06: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3/19 9:06:19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Post By:2008/3/19 9:06:5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3/19 9:06:53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