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了,他都八十了。
大地的冰雪融化了。
阳历的新年,他参加了人民大会堂里的新春茶话会。新朋老友相聚,其乐融融。
过春节的时候,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了他的家里拜年。这位贵客来得不是时候,其时,在新搬过家依然很小的房间里,沈先生正在清理一些资料,书啊,报啊,刊啊,图片啊,插图啊,旁人看似乱糟糟的,而在他看来是有条不紊的,所有的平面都摊满了,政治局委员同志都不好下脚了,都没坐的地儿了。
先一年,他耗费了后半生大半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原为资料)》在香港得已出版;
先一年,他应邀访问了美国,在一些大学作了讲演,他在那里有许多“粉丝”;
他的半个世纪前的作品陆续在出版。湖南、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与三联、江西等多家出版社计有二十多种作品集子要在这一个时候出来。
当然,海外在这之前和之后也出了不少。
“沈从文热”正在海内外兴起。
他倒是不习惯了。一次次给他的研究者泼冷水,不要研究我,将来会没有出路的;一次次给朋友们和读者写信说,都是习作,不要以为如何不得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在表侄、画家黄永玉的劝说和帮助下,沈先生回到了故乡凤凰。故乡热情款待了这位久违了的游子。
此时,在北京的颐和园,柳丝应该是刚绽出一点点鹅黄,湘西花开花落,已是春深了。
他是和着春天的脚步到来的。真正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啊!只是这一份青春的成色是有点太老了些。
虽然他原先白净的脸上有了老人斑,但他的面容饱满,步履稳健。
他在故乡的土地上漫游。
他去县民族工艺厂,伸手抚摸机架上的那些漂亮的织花;
他和乡亲们驾着小船在沱江泛流,岸边的水碾、吊脚楼、青山一齐迎了过来;
他去了苗乡赶场,在拥挤的人流中端了一碗放有红辣椒粉的米粉当午餐;
他在古迹前游览,在河坝上野餐,在童年坐过的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听课……
在至今还保存完好的清初黄丝桥古城,他碰上了三个苗族老太太,他一个个地问着:“你多大了?”
“八十一。”
“你呢?”
“八十二。”
“她呢?
“八十七。”
问完,沈先生笑了:“哈哈,看来我还是小弟弟哩。来,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后来,他去了州府,看了那里的博物馆。在一个类似茶峒的渡口边,他坐了下来。一根篾缆系着两岸,上面连着一只小小渡船。一条碧绿的溪水,镜面一样的溪水映着边上的吊脚楼和山色。他在石阶上坐下,好像要醉了,猛地说了一句:真想死在这里。话出口,吓了大家一跳。
再后来去了张家界,坐在金鞭溪的大石头上,他又说了一句:真想死在这里。
故乡的山水永远是他心灵的归宿。
这一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沈先生参加了王震率领的访问团去了日本。在日本他不忘本行,去参观了东京博物馆。还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们进行了座谈。日本也有他的“粉丝”,他和那些新朋友们吃了一回简单而快乐的午饭。
12月六日,沈先生做了一个决定。花城和三联出版他的十二本文集,收到九千七百元稿费,他交这笔钱捐给了他曾经上过小学的凤凰文昌阁小学。
这此,他给学校的样第写了一封信。
校长先生:
我上星期了一万元人民币到县里,托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代收,并至函说明:这笔款是我捐赠给本县文昌阁小学使用。款汇到时,希望能邀校中一二年长负责同志,斟酌情况,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宿舍……
十二月二十八日,是沈从文先生八十寿辰,他新调到不久的单位的领导专门来到他家为他祝贺生日。几个比较要好的作家朋友想聚一聚,要给他做一个生日宴会。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躲到了一个亲戚家里,吃了一碗面条了事。
沈从文的六十、七十、八十,都是一些不平常的日子。
他终生没有退休,他工作到了他最后的一天。
他走的时候,走得非常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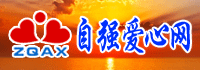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466
精华:3
积分:4597
金钱:9721
金币:0
魅力:2609
威望:0
登陆:226
注册:2006/12/13 16:13:17
近访:2011/9/16 0:41:56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466
精华:3
积分:4597
金钱:9721
金币:0
魅力:2609
威望:0
登陆:226
注册:2006/12/13 16:13:17
近访:2011/9/16 0:41:56
在线:
 Post By:2007/5/4 12:11: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5/4 12:11:03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466
精华:3
积分:4597
金钱:9721
金币:0
魅力:2609
威望:0
登陆:226
注册:2006/12/13 16:13:17
近访:2011/9/16 0:41:56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466
精华:3
积分:4597
金钱:9721
金币:0
魅力:2609
威望:0
登陆:226
注册:2006/12/13 16:13:17
近访:2011/9/16 0:41:56
在线:
 Post By:2007/5/4 12:11: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5/4 12:11:16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466
精华:3
积分:4597
金钱:9721
金币:0
魅力:2609
威望:0
登陆:226
注册:2006/12/13 16:13:17
近访:2011/9/16 0:41:56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466
精华:3
积分:4597
金钱:9721
金币:0
魅力:2609
威望:0
登陆:226
注册:2006/12/13 16:13:17
近访:2011/9/16 0:41:56
在线:
 Post By:2007/5/4 12:12:3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5/4 12:12:34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