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子已被锁定
接到一个女孩子的信,问我有没有看过美国电影《LegallyBlonde》,说她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被上台大的男朋友甩了,现在她正昏天黑地啃书,非考进台大不可,而且要进她男朋友那一系,在系里跟他拼,然后在那男生回心转意的时候,把他甩掉,报一箭之仇。
才看完信,就跟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学生吃饭,闲聊中提起那部电影。
“我也看过啊!”女生一笑,“宿舍的同学一起去看的,讲一个女生被男朋友甩,再甩她男朋友的故事。”
“于是那女生报了一箭之仇?”我问。
女学生一怔,笑笑,“怎么说报仇呢?起先男生去东岸念哈佛,女生在西岸,一东一西,根本不在一个世界,当然会吹。”
“后来女生不是也上哈佛了吗?男生不是也回头了吗?”我又问。
“男生是回头了,可是他不如女生,比女生差多了。女生还没毕业就出庭当律师,那男生却还像个小朋友,他们当然会吹,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儿子初中时,念附近的天主教学校,交了一帮朋友,一下课就来家找。
可是上高中,我们经过一番挣扎,送他进了远在曼哈顿的史岱文森高中,每天单单上下学搭车就花掉三个钟头,渐渐地,附近的朋友不来找他,他也不再去找当年的死党。
“你平常是因为没空,为什么放假也不去找老同学玩玩呢?”问他。
“他们太不成熟了。”儿子撇撇嘴,“有一天我说去新泽西州的大冒险乐园,他们居然把眼睛瞪得好大,说:‘什么?那多远呐!’你说好笑不好笑?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少年时去爬山,也遇过这样的情况。
一群爱登山的朋友,由台北近郊的大屯山、观音山和鸟来内山开始登,愈爬愈高,终于上了合欢山、大雪山和玉山。
队伍里从起初就有一对情侣,总是相互照顾,可是当大家愈爬愈高,他们却吹了。
原因是每次只要过了一定的高度,那男生就脸色惨白,好几次被紧急抬下山。可是只要下到一定高度,他就立刻“还魂”,生龙活虎起来。
反倒是那女生一点没有“高山症”,起先她都陪男生留下来,目送大家继续爬,后来男生劝她也去,反正没多久就下来了,她才勉强同意。
到高山是不能多想事的,一方面因为危险,不能分心;一方面因为缺氧,脑袋不灵光。那女生一上山,就好像把男生全忘了。
有一天,从山头下来,一群人满身泥泞汗水地走进休息站,发现等在下面的男生正在跟另一个女生喝咖啡。
从那天起,再没有看见男生,倒是女生继续爬,而且又交了个可以相互扶持的“山友男朋友”。
“没办法!”女生说,“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参加旅行团到挪威和瑞典去,起先团员彼此都陌生,只跟自己人在一起,渐渐形成小圈圈,又渐渐打成一片,一起唱歌、一起逗笑、一起跳方块舞。我的女儿拉小提琴,我秀我的写生,南非的一对夫妻唱他们的国歌,尤其到三个星期行程要结束的那几天,大家更是依依不舍。
“最后的晚餐,”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太跑来搂着我和妻的肩,感慨地说,“我真不懂,大家这么好,为什么每个旅行团结束之后却都一下子全不见了,而且失去联络,这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她不断地摇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问题是,旅行团结束了,虽然交换了地址,我却没收到她的信,几度想提笔写个卡片给她,也终于没那么做。
是啊!为什么旅行团里交的那么好的朋友,一朝分散就多半失去联系?不是说好,大家还要一起去旅行吗?不是有人讲要写旅行心得寄给彼此吗?不是有人要把照片从网上送给每个人吗?
言犹在耳,为什么全说话不算话?
或许因为旅行太快乐了吧!把俗世的一切全抛在脑后,大家尽情地放松、尽情地游玩,好像在天堂一般。
只是旅行结束,也就是坠入凡尘的时刻,大家重新面对的是沉重的工作、繁琐的家务和纷乱的人情,于是仿佛饮了忘川之水,忘却了天上的一切。
就像那攀在巅峰的女生,面对的是危险的峭壁和稀薄的氧气,她怎么能够去思索她在山腰喝咖啡的男朋友?
只因——
他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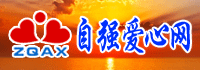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Post By:2007/7/21 7:58:0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7/21 7:58:02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