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体育明星桑兰在其博客中,连续批评城市无障碍出行公共设施匮乏,尤其是无障碍车位被挤占的问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2008年的残奥会,让全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顶峰,热潮过后,我们的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注度是否衰减?无障碍公共设施是否得到了保留?残障人士的保障还存在哪些问题?本报专访桑兰。
无障碍车位被挤占严重
新京报:最近你在博客中,批评残障人士的无障碍出行公共设施,尤其是无障碍车位问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谈这个问题?
桑兰:我是最近发现了问题才提出来的。
去年北京奥运会要坐国际航班,我去了3号航站楼,一进停车场,就看到无障碍车位,很接近电梯,也有锥筒和拉线杆保护,有工作人员管理。当时我就把伤残证给工作人员看,看过之后他就把车位安排给我们,很高兴。
但是今年5月去三亚,在首都机场就遇到所有的无障碍车位全部被占用的情况。在停车场转了好多圈都找不到位置,我很难判断这些车是否是接送伤残人士的。
再一次去3号航站楼是这个月的16号,我要飞去杭州录节目,结果所有的无障碍车位都被占用了。去年和今年的差别是一天一地。
可能去年是奥运会,人人都激情澎湃,各方面监管力度都很大,但这样的意识和激情能够延续下去该多好啊。
新京报:你还提出北京的无障碍出租车太少的问题,这方面你的体验是什么?
桑兰:我是使用了才知道它太难预订了。
无障碍出租车是去年北京残奥会举办的时候投入运营的,数量特别少,我坐过的那种江陵全顺无障碍车,全北京只有10辆。
那天我要去看比赛,听说有这种出租车就打电话预约,但根本约不到,幸好家对面的康复中心停了一辆,就把车叫过来,价格很贵,包车从洋桥往返鸟巢要300多块。
去年10月,我还用过一次,提前3天预约才约上。记得回家的路上,停了一下,旁边一个妈妈推着一个坐轮椅的孩子,说,“太好了,现在有这个车可以坐了,那我就可以带你出去玩了”。
所以,这种车的需求是存在的,毕竟全国的残障人士总数已经超过了8300万。
赋予残障人士平等出行权
新京报:你呼吁的一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比如很多人不知道有一种特殊车位存在,占用了也浑然不觉。
桑兰:3号航站楼的工作人员也说,没办奥运会前,根本就不了解残障人士出行的需求,因为要完成对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员工亲身坐轮椅扮成残障人士逐一体验,这就是一个从不了解到慢慢了解的过程。
我受伤后在美国治疗,去过一趟迪斯尼,有很多项目我是可以玩的,而且也都有无障碍设施。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每个地方都去排队,没有走无障碍通道。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排在两个美国小男孩的后面,哥哥应该是六七岁,弟弟是三四岁的样子,看到我坐轮椅,哥哥马上把弟弟拉到一边,让我先过。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教育成果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
新京报:你能不能用具体的生活经验,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无障碍”?
桑兰:比如说我要去餐馆吃饭,我能不能自己从家门口到餐馆。目前我还没有独自出行过,因为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无障碍环境允许我这样做。
比如总有些地方没有无障碍通道,简单说就是没有斜坡或电梯,都是台阶,或者斜坡的坡度太大我自己根本上不去,但其实这个坡道的坡度和宽度是有国家标准的。
比如去餐馆,我的腿常常放不进桌子下面,因为轮椅的高度常常超过了桌面的离地间隙。
还有,如果出远门,我需要有人帮我驾车,或者预约方便的无障碍出租车,还需要无障碍停车位。
电梯最好有直梯,直梯里需要有低位楼层按钮和镜子,这个镜子也有个国际标准,方便残障人士在出电梯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看到背后有没有障碍物。
公共场所还需要有无障碍卫生间,就是洗手池和烘干器都很低,马桶两侧有扶手,空间很大的那种,甚至还要有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公用电话、饮水机等。
什么叫无障碍?就是赋予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这个是第一步。
写博客是我的“游说”方式
新京报:你说美国“超人”克里斯托弗·里夫是你的精神支柱和榜样,“想起他为美国残障人士游说美国国会做的那些努力,我还很渺小”。里夫的经历和做法是否成为你的某种导引?
桑兰:里夫是我非常敬佩的人,对我影响很深。
他骑马意外受伤,高位截瘫比我还严重,戴呼吸机,一动都不能动,但他一直以微笑示人。
他不断游说美国国会,为残障人士争取福利,包括支持全球的脊髓干细胞研究。他和他的夫人成立的丹娜·里夫基金会,为改善残障人士福利做了很多工作。
新京报:你现在用博客去引起公共空间的讨论,或者用更为个人化的渠道去影响一些残障人士保障方面的决策,也算是你游说的方式吧?
桑兰:是的,名人会有一种权力,我会善用这种权力去呼吁这个社会,为弱势群体争取他们的福利。我在博客里反映问题,就是我这方面的努力。
今年3月份“两会”的时候,我还在博客里写过一封给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建议康复治疗进入医保范围,因为不光是我这种高位截瘫患者,很多病患在康复期间都会出现并发症或肌肉萎缩现象,但现在的医保对这个部分还是空白。
我现在还在准备给交通部、公安部和残联写信,希望在无障碍设施以及残障人士优先权保障方面能够得到改善,比如无障碍车位的停车标准、如何执行、如何核对,希望用我和更多人的声音尽可能改变这一切。
社会需要我这样的民间力量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更好的做事情?
桑兰:我还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不过我刚刚成为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的委员,这样我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也能接触到一些体育卫生界别的决策人士。
今年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我也加入了世界青年领袖,筹备和另外一个青年领袖一起做一些关于推广无障碍设施的工作。
我想除政府之外,也需要像我们这样一些民间的力量,来推动残障人士保障事业。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力,才能把一个事业做起来,我的梦想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新京报:你还提到要用自己的基金会投入无障碍出租车?
桑兰:对,除呼吁之外,也会从我的基金会开始做。
我受伤的时候中国运动员是没有保险的,因为我的事情影响很大,国家体育总局就和民政部批准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开始给运动员上保险。
我受伤之后也一直想建立一个民间的基金。因为我受伤之后,美国这个运动会因为买了保险,产生了1000万美元的医疗保障金,我在美国治疗期间发生的费用,是在这个保险范围里的。当时我就想,如果其他运动员受伤了,没有保险怎么办?
新京报:你给总理的公开信最后有反馈吗?
桑兰:总理应该是看到这封信了,因为中华康复医学会的网站上后来刊载了一篇文章,提到我给总理的这封信,并表明总理做了批示,卫生部医政司正在开会研究康复治疗纳入医保的相关问题。
我最近也注意到,卫生部公布的医疗机构改革方案中,在最后部分也提到了康复。
呼吁并不是为我自己
新京报:近期你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反映现在每个月的收入,除了应付日常开销,还要承担康复治疗,并不宽裕,是不是这个建议必要性的现身说法?
桑兰:康复医疗没有纳入医保,我现在的康复补贴是个人和单位协商的结果,因为我的身份还有特事特办的成分。浙江省体育局的领导批条子,单位出政策,决定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的康复补助。
而我的工资是一个月1600块,保姆费600块。
此外我吃的药因为都从美国买,可以在美国那1000万医疗保险金里扣除,其他发生在中国的医药费,那个保险金就管不了了。
这些钱对我维持治疗来说,是不够用的,所以还要靠自己去工作来赚些钱,比如给杂志报纸写专栏,给一些电视台、网站做主持人,或在博客上做些广告之类来维持。
新京报:在博客里你也提及,“这么多年来很多残障人士是给我‘白眼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生活得好,有的是钱,甚至有1000万美元”。你怎么面对这些“白眼”?
桑兰:不理解的人肯定会有。1000万美元只是美国那个运动会的保险金,并不是我个人的,它只负责我脊髓损伤那个方面在美国的治疗费用。
前段时间也有电视节目,说桑兰的形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保姆门事件”,包括我现在谈的“无障碍车位”,有人觉得我很挑剔。
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这种质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为了我自己,我没必要这么做,毕竟我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经被照顾得很好了。
桑兰
原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在1998年7月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一次跳马练习中不慎受伤,造成高位截瘫,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表现出顽强意志,在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并成为2008年北京申奥大使之一,又于2008年北京奥运官方网站担当特约记者。
无障碍环境
■ 链接
无障碍环境
包括物质环境、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
物质环境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城市道路、公共建筑物和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应方便残疾人通行和使用,如城市道路应满足坐轮椅者、拄拐杖者通行和方便视力残疾者通行,建筑物应考虑出入口、地面、电梯、扶手、厕所、房间、柜台等设置残疾人可使用的相应设施和方便残疾人通行等。
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公共传媒应使听力言语和视力残疾者能够无障碍地获得信息,进行交流,如影视作品、电视节目的字幕和解说,电视手语,盲人有声读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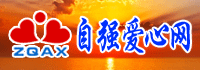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1562
精华:0
积分:15608
金钱:12839
金币:13
魅力:9186
威望:0
登陆:258
注册:2008/9/12 13:46:52
近访:2020/3/3 9:27:50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1562
精华:0
积分:15608
金钱:12839
金币:13
魅力:9186
威望:0
登陆:258
注册:2008/9/12 13:46:52
近访:2020/3/3 9:27:50
在线:
 Post By:2009/11/3 12:02: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11/3 12:02:21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