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子已被锁定
妈并不是个理想的妈妈。
妈个头矮小,长相平常,反应有些迟钝,据说十八岁时跟着姥爷来镇上和爸相亲,自己跳不上自行车后座,还是姥爷给抱上去的。
妈做什么都慢,总赶不上别人的趟。为这,被爸说骂过很多次。可无论爸如何为此嘲笑、发急、动火,妈一辈子也没改过来。
慢,是妈的本性。
妈不是个很会照顾孩子和家禽的人,她爱忘事,干活又磨蹭。一顿饭,别人家三下五除二做好吃了洗涮完,妈的饭还在进行一半中。
所以,家里除了耐饿的猪,其他的家禽,总不能皮滑毛亮得养大。小时候,自家鸡生的蛋,自家腌的咸蛋等诸如此类的吃食,记忆里寥寥可数。
家里也很少养羊。问妈为什么不养羊,妈就说烦听羊叫。一叫就凄凄惨惨的,听着烦心。但后来有一年,家里不知谁给了一只羊,就养下了。
白白的小羊,用一条绳栓在院的一角。我没注意羊的叫有多烦人,只看妈来来回回走着为它张罗起圈,也没再提羊叫声很烦人的老话。妈拿草喂羊时,总笑咪咪地唤着小羊,妈和羊都仿佛很受用的神情。
小羊和我一样,每天悄悄成长。
没过多久 ,羊竟然病了。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妈不在,锅也是冷的。我扒找出冷饭剩菜填饱肚子,就调头回学校。路上,遇到了正抱着小羊的妈。
妈看到我,有些着急:“饭还没做呢。你就去上学了啊?”
我说:“吃了呢,吃饱了。”
妈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看怀里的羊,又看看我说:“羊得了毛病,不吃不喝,拉稀拉得站都站不住。我是抱它去畜医那看了下,刚回……”
我点了点头,就赶着上学去了。
接下来,妈带着羊一天一趟往畜医处跑。几天后,羊终于又站在院子一角急霍霍地吃草了。妈很高兴。邻居大妈来我家串门,和妈说闲话:“你高兴个啥,给羊看病的钱都值俩羊钱了。”
妈不恼,只是笑着:“到底是条命啊。”
邻居懒得争论,放下这个话题扯别的,一旁的我抬头看了又看妈。那一刻起,我对妈的看法忽然有了些转变。
后来我和弟弟双双求学异乡,爸也去了外地打工,家里就只剩下了妈。一直担心妈一人在家会寂寞。却不料,妈收留了一个外地拾荒的老姑婆在家,据说两人相处得挺乐和。除了想起我和弟弟的时候,妈会止不住落泪。
亲戚嫌弃妈的做法,说没事把自家弄成了垃圾场。妈的弟妹没少说她,而妈依然是那样没脾气地笑着:“怪难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于是她依然我行我素。
妈平日最怕别人提起一件事,和我有关。妈二十四岁结婚,二十五岁生下我。
妈从小怕血,无奈怀我时一直病患在身。待生我前夕,已气脉微弱危在旦夕。医生给她输血以增加体力,或许是血型的匹配有些小问题,或许是她睁开眼被那吊瓶里的鲜血吓倒了。我出生后有一段日子,妈的精神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我长大后,姑姨舅叔等和我讲过很多次。说那时我们母女出院回到家,妈精神有些不正常。有事没事总把襁褓中的我从床这一头丢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丢到这一头。说完他们都笑:“没想到啊,丢来丢去的,也丢大了。”
那一次,小姨和小舅又说到这,正大笑的时候被妈听到了。很少发火的妈把他俩狠狠骂了一顿:“说些什么不好,闲得乱咧咧。” 小姨和小舅对着眨眨眼,笑完了最后一下,打住不说了。我诧异妈极少发的火,妈转头出屋的时候偷眼看我,视线正着时,我响亮地叫声:“妈”。妈就笑了。
第二次也是亲戚们聚在一起,热闹地说着话,话题到我的时候,堂姑妈禁不住又说起我刚出生的时候,干瘦得像个小老头,被包在襁褓里。在床上要换头睡觉了,妈就抱起来,朝床那头一摔;要换回来了,再抱起来往这头一摔。亲戚们感慨地哄笑。
又让回屋拿开水瓶的妈听到了。这次妈没骂人,只是急了脸恨恨地说:“都拿这当事说了?谁的孩子谁不知道疼,要是摔,孩子还能活命?”妈脸上的委屈和一本正经的辩解,满屋一时无法应对。我站起来拉妈的手,带着刚才的笑:“妈就是摔,也没事。自己的小孩,能疼就能摔。再怎么摔我还不是长大成人了嘛。”妈的气在听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时已消了大半,“再说,我一点也没觉得疼哪。”一屋人被我说得又哄笑了。我拉着妈的手一起去灌水,妈两眼里有刚才急出的泪花,却也被逗笑了。我的鼻子却在偷偷发酸
娘心如棉,并非独暖我身。但唯愿,我心亦如棉,温暖妈以后所有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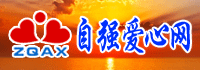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等级:论坛版主
帖子:777
精华:1
积分:7341
金钱:11571
金币:0
魅力:4260
威望:0
登陆:27
注册:2007/6/20 9:59:29
近访:2009/4/24 13:42:38
在线:
 Post By:2007/8/30 21:51: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8/30 21:51:19 [只看该作者]

